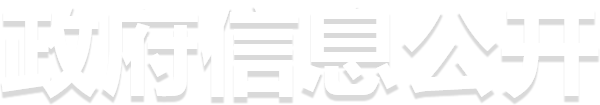
- 索 引 号: sm09108-1800-2025-00018
- 备注/文号: 将政行复〔2025〕9号
- 发布机构: 将乐县司法局
- 公文生成日期: 2025-09-23
申请人1(原被处罚人):廖某某,女,某年某月某日出生,身份证号码:350428XXXXXXXXXXXX,住福建省将乐县水南镇。
申请人2(受害人):李某某,男,某年某月某日出生,身份证号码350428XXXXXXXXXXXX,住福建省将乐县。
法定代理人:李某某,男,某年某月某日出生,身份证号码:350428XXXXXXXXXXXX,住福建省将乐县。
委托代理人:包某某,系李某某女儿,女,某年某月某日出生,身份证号码330329XXXXXXXXXXXX,住福建省三明市将乐县。
被申请人:将乐县公安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5********8498XG,住所:福建省三明市将乐县古镛镇新和路9号,法定代表人:雷祥源,职务:局长。
申请人1因不服将乐县公安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将公(城关)行罚决字〔2025〕00145号),于2025年7月17日向将乐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本机关于2025年7月18日依法受理,适用普通程序审理。2025年8月14日及8月15日,本机关以座谈会的方式分别听取利害关系人(受害人)委托代理人和当事人意见,2025年8月19日,申请人2因不服将乐县公安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将公(城关)行罚决字〔2025〕00145号)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经审查,本机关认为上述两起复议案件涉及同一行政行为,且事实和法律问题具有关联性,符合合并审理的条件,本机关决定将两起案件合并审理,并于8月20日告知各方当事人,现本案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1请求,撤销将乐县公安局于2025年7月17日作出的将公(城关)行罚决字〔2025〕0014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申请人1认为,被申请人作出上述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错误。首先,申请人1作为申请人2的老师,坐在申请人2的背后右手握住申请人2的右手拿笔,左手压住申请人2的左手压住写字本,教申请人2写汉字,这是申请人1作为老师手把手的教学写汉字,是尽心尽责的。其次,因为申请人2本身是特殊儿童,属于自闭症患者,在申请人1手把手的教申请人2写汉字时,口里一直发出“啊……”的声音,不够专注,此时申请人1轻声劝说“不要叫”,因为申请人2又发出“啊”的声音,申请人1左手四指并拢微曲,拇指尖贴到食指第二节(手掌空心)轻按申请人2的前额以提醒,并说“啊……,啊你个头,没写完就不能回家”,并非处罚决定书中认定的“手指并拢的方式朝申请人2左侧面部击打一下。”再次,现场证人仅有余某娟,现场并无其他人,并非处罚决定书认定“余某娟、张某某、郑某焱、郑某龙、余某、包某某等人的证人”,其中“张某某”是谢某某(是申请人2的母亲),“包某某”是施某某。第四,处罚决定书存在两次重复叙述“未造成危害后果”的认定与“伤情记录表”存在矛盾。由于申请人2的父母到处上访,申请人2父母提出不合理赔偿诉求,要求赔偿人民币50万元,认为被申请人迫于信访压力,虚构相关事实对申请人1进行处罚。
申请人1认为,其涉事行为不构成应当受到治安处罚的行为要件。一是行为性质存在争议,主张击打行为系“教学管理中的轻微惩戒”,非主观恶意殴打,且未造成实际伤害,决定书也载明“未造成危害后果”。申请人1的行为是“因学生不配合教学引发”,具有即时性、短暂性,仅持续1分钟,且仅有一次,“申请人1左手四指并扰微曲拇指尖贴到食指第二节(手掌空心)轻按申请人2的前额以提醒”即停止。二是证据不足。对监控视频的证明力提出质疑,需核实视频是否清晰显示击打力度、是否超出正常教学管理范围。公安机关已排除2024年12月16日类似行为为殴打行为。三是特殊情境因素。申请人2为残疾未成年人,教学过程中可能存在沟通障碍,教师行为需结合特殊教育场景综合评判。
申请人1认为,其行为不符合“殴打他人”的构成要件,被申请人对涉事处罚违反处罚适当性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条:治安管理处罚应以事实为依据,与违法行为的性质、情节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申请人1认为涉事行为未侵害申请人2的健康权,不符合“殴打他人”的构成要件,不存在造成身体疼痛或轻微伤害的情形。申请人1即使是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九条规定,但认为其有主动投案和如实陈述,且行为未造成后果,属于情节特别轻微的,符合应减轻或不予处罚的情形,被申请人作出对申请人1处以行政拘留五日、罚款壹佰元的处罚,违反处罚适当性原则。
申请人1提供相关证据:1.处罚决定书复印件;2.申请人身份证复印件。
申请人2请求:1.撤销将公(城关)行罚决字〔2025〕0014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2.责令被申请人重新作出行政处罚决定;3.责令被申请人在重新调查时,对受害人耳蜗、脑部、脸部损伤及心理损害进行补充鉴定;4.对本案执法程序及适用法律进行全面审查,并追究相关责任人员责任。
申请人2法定代理人认为,处罚决定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一是决定书一方面认定现有证据无法证实申请人1殴打申请人2,另一方面又确认申请人1对申请人2实施击打一次,存在自相矛盾。二是原决定书仅表述使用左手手指并拢击打一次,与客观证据严重不符,现场监控视频清晰显示,违法行为人连续三次掌掴申请人2面颊,且拉至非监控区域中孩子的哭喊声很大,合理怀疑老师还在继续殴打学生,从查看监控当天有监护人、学校负责人都可证。三是现场监控、伤情照片、诊断记录、验伤报告等关键证据未在决定书中载明,亦未向申请人2及其监护人完整出示,导致事实认定严重缺失(见附件检查报告)。四是处罚不当。2024年12月16日,申请人1在同一教室再次对申请人2实施体罚,两次殴打时间间隔不足七个月,属连续侵害,应认定为“多次殴打不满十四周岁的残疾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二款第(二)项加重处罚情形。
申请人2法定代理人认为,被申请人适用法律错误,存在处罚畸轻的问题。一是受害者系未满14周岁的残疾未成年人(年仅7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二款第(二)项“殴打、伤害残疾人或者未满十四周岁的人”的,应当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并处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被申请人仅给予行政拘留五日并罚款100元,明显低于法定下限。二是被申请人错误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九条“情节特别轻微”条款,忽视受害人特殊身份及案件社会危害后果,属适用法律错误。三是该心理损害虽无法以体表伤形式固定,但已明显影响受害人社会功能,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一百一十条所指“精神损害”。
申请人2法定代理人认为,被申请人程序违法,侵害受害人陈述申辩权。一是处罚前未书面告知受害人及其监护人有陈述、申辩及申请听证的权利。二是未将鉴定意见、现场监控等关键证据向申请人2及其监护人出示并听取意见。三是决定书送达程序存在瑕疵,未向受害人监护人送达副本,导致申请人2无法及时行使救济权。
申请人2法定代理人认为,处理结果显失公正,损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申请人1身为特殊教育中心教师,对残疾未成年学生实施暴力,社会危害性大、负面影响恶劣。被申请人却以“情绪急躁”“未造成危害后果”等理由从轻处罚,显失社会公平正义,亦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的立法精神相悖。
申请人2法定代理人提供相关证据:1.处罚决定书复印件;2.申请人残疾证明、出生医学证明;3.监护人身份证明;4.两次伤情照片;5.诊断病历及相关费用发票等。
被申请人认为,本案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
被申请人称,本案由申请人2的法定代理人李某某于2025年5月20日报案至被申请人处,被申请人于同日立行政案件调查,经依法查明,于2025年7月17日对申请人1作出行政处罚决定。2025年5月16日下午,申请人1在将乐县某某教育中心二楼个性化训练室一内教申请人2写字,因申请人2系持有残疾证的自闭症儿童,在写字过程中无法较好地配合,导致申请人1情绪急躁。17时12分许,申请人2突然大声喊叫,申请人1便采取手指并拢的方式朝申请人2左侧面部击打一下。2025年5月20日晚申请人2家长带申请人2至将乐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报案。申请人1于2025年5月21日下午主动至将乐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投案。2025年6月4日,城关派出所依法委托将乐县公安局物证鉴定室对申请人2伤情进行鉴定,因检材/样本不具备鉴定条件,同日将乐县公安局物证鉴定室作出不予受理决定。申请人2家属另控告,2024年12月16日申请人1在某某教育中心曾对申请人2实施了殴打行为。经调查,该时间段现场视频监控已被覆盖,无法提取,且申请人1当时与申请人2系一对一教学,无其他人员在场,相关证据无法证实,故无法认定该违法事实存在。
被申请人认为,申请人1于2025年5月16日下午使用左手击打申请人2左侧面部的行为已构成殴打他人。经查,申请人2系未满十四周岁的残疾未成年人。申请人1所实施的殴打行为系因申请人2不配合教学引发,对申请人2实施击打一次后便停止,未造成危害后果,情节特别轻微,应减轻处罚,案发后申请人1主动投案并如实陈述自己的违法行为,应减轻处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二款第二项,第十九条第一项、第四项之规定,对申请人1处以行政拘留五日,并处罚款壹佰元。
被申请人认为,申请人1所称被申请人认定事实错误的理由不存在:
1.申请人1提出《行政处罚决定书》中认定的“采取手指并拢的方式朝申请人2左侧面部击打一下”事实认定错误的理由不存在。经调取案发现场监控视频,2025年5月16日17时许,申请人1在某某教育中心二楼个性化训练室一内教申请人2写字,17时11分26秒,申请人2发出“啊”的声音,监控视频中申请人1并未轻声劝说让其不要叫,17时12分09秒,申请人2突然大声喊叫发出“啊”的声音,17时12分11秒,申请人1采取左手手指并拢的方式朝申请人2左侧面部击打一下,存在明显发力,监控视频中可以听到击打发出“啪”的一声较大声响,与申请人1提出的“轻按申请人2的前额以提醒”明显不符。申请人1提出采取“坐在申请人2背后,右手握住申请人2的右手拿笔,左手压住申请人2的左手压住写字本,教申请人2写汉字,尽心尽责”与本案认定的殴打事实无关。
2.申请人1提出的“现场证人仅有余某娟”,行政处罚决定书中的谢某某、郑某焱、郑某龙、余某、包某某等人不属于本案证人的理由不存在。该案中余某娟在申请人2被殴打后有到达案发现场,可以证实案发后现场情况,系现场证人。谢某某系申请人2母亲,可以证实申请人2被殴打后情况。郑某焱、郑某龙系某某教育中心负责人,二人均对该案情况有所了解。余某系残联工作人员,其在案发后有到某某教育中心查看现场的监控视频。包某某系申请人2的姐姐,其主动到将乐县城关派出所反映2024年12月16日下午申请人2被申请人1殴打情况。以上人员均对该案情况有所了解,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三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凡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故余某娟、谢某某、郑某焱、郑某龙、余某、包某某均系本案证人。申请人1提出的“证人中“张某某”是谢某某”问题系笔误,属轻微瑕疵,不影响案件事实认定。民警在发现该问题后,已立即纠正并重新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申请人1,但申请人1收取后拒绝签字,申请人1在复议中提供的系修改前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该案生效文书应以修改后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为准。
3.申请人1提出的处罚决定书中存在两次重复叙述“未造成危害后果”的认定与“伤情记录表”矛盾的理由不存在。“伤情记录表”是公安机关办理殴打他人案件中第一时间记录伤情的重要证据材料,该案“伤情记录表”中记录申请人2左边鬓角处有一道2至3公分的划痕。在后续调查过程中,申请人1陈述称该划痕确系其造成,但无法确定系在殴打过程中造成还是其在为申请人2擦鼻涕过程中造成,现场监控视频及询问笔录等证据均无法证实划痕形成具体原因,故该情况无法认定为殴打造成的危害后果。“伤情记录表”属过程性、阶段性材料,违法事实及后果最终在处罚决定书中予以认定,且处罚决定书认定“未造成危害后果”更有利于复议申请人1,行政处罚决定书的认定的“未造成危害后果”与“伤情记录表”不存在矛盾问题。
4.申请人1提出的由于申请人2父母到处上访,被申请人为满足申请人2父母私欲(要求赔偿人民币50万元),及处罚申请人1,就东拼西凑乱写事实的理由不存在。民警在该案调查过程中严格依法履职,及时、客观、全面地收集了相关证据,对案件的原因、经过和后果进行了充分的调查,该案所认定事实客观存在,经调查属实,证据确实、充分,申请人1提出的“申请人2父母到处上访”与本案事实认定及处罚结果无关,更不存在其提出的被申请人为实施处罚而东拼西凑乱写事实情形。
被申请人认为,申请人1认为其在该案中的行为不构成行政处罚要件的理由不存在:
1.申请人1提出其击打行为系“教学管理中的轻微惩戒”,非主观恶意殴打,理由不存在。《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对教育惩戒作出了明确规定,其中第八条规定的教育惩戒包括:(一)、点名批评;(二)、责令赔礼道歉、做口头或者书面检讨;(三)、适当增加额外的教学或者班级公益服务任务;(四)、一节课堂教学时间内的教室内站立;(五)、课后教导;(六)、学校校规校纪或者班规、班级公约规定的其他适当措施。第九条规定的教育惩戒包括:(一)、由学校德育工作负责人予以训导;(二)、承担校内公益服务任务;(三)、安排接受专门的校规校纪、行为规则教育;(四)、暂停或者限制学生参加游览、校外集体活动以及其他外出集体活动;(五)、学校校规校纪规定的其他适当措施;第十条规定的教育惩戒措施包括:(一)、给予不超过一周的停课或停学,要求家长在家进行教育、管教;(二)、由法治副校长或法治辅导员予以训诫;(三)、安排专门的课程或者教育场所,由社会工作者或其他专业人员进行心理辅导、行为干预。申请人1所实施的击打行为不属于上述任何一种教育惩戒措施。且申请人1在第一次、第二次询问笔录中均陈述,因急躁,未控制住情绪,故打了申请人2,其存在主观发泄情绪的故意,案发监控视频显示,2025年5月16日17时24分25秒,申请人1与余某娟在对话过程中,余某娟使用本地话问申请人1:“那监控里面你没有去打他吧”,申请人1回答称“有哦”,并比划了几下当时的动作,可以证明此时申请人1已经意识到自己的行为不当。申请人1提出其行为系因学生不配合教学引发,具有即时性、短暂性,仅持续一分钟,且仅有一次,未造成实际伤害,该部分内容已在处罚决定中认定为情节显著轻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九条第一项之规定对申请人1减轻处罚。申请人1采取左手手指并拢的方式朝申请人2左侧面部击打一下,存在明显发力,监控视频中可以听到击打发出“啪”的一声较大声响,与申请人1提出的“轻按申请人2的前额以提醒”明显不符。
2.申请人1对案发监控视频的证明力提出质疑,认为证据不足理由不存在。被申请人处民警于2025年5月20日开具调取证据通知书《将公调证通知书〔2025〕00011号》,并于2025年5月21日前往将乐县某某教育中心调取涉案监控视频,涉案视频系被申请人处民警直接从该教育中心监控系统下载刻录,该监控视频能清晰反映申请人1于2025年17时12分11秒,采取左手手指并拢的方式朝申请人2左侧面部击打一下,监控视频中可以听到击打发出“啪”的一声较大声响,击打过后申请人2便开始号啕大哭,可以判断出该次击打存在明显发力,结合申请人1在第二次询问笔录中陈述的该行为已经超出了对待此类自闭症学生的教学举措,在第五次询问笔录中陈述的该击打行为对教学没有帮助,综合认定该行为不属于正常教学管理范畴,该监控视频证据来源、形式、程序均符合法律规定,监控内容所能证明的事实与待证事实一致,不存在证明力弱、证据不足问题。对于申请人2家属控告的,2024年12月16日申请人1在某某教育中心曾对申请人2实施了殴打行为。因该时间段现场视频监控已被覆盖,无法调取,且当时申请人1与申请人2系一对一教学,无其他人员在场,相关证据无法证实,故无法认定该违法事实存在。
3.经调查,申请人1非将乐县教育系统在编在岗教师,其所工作的将乐县某某教育中心学校类型为其他,不属于《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第二条所规定的普通中小学校、中等职业学校,故其所实施行为也不在《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调整范畴。即使系普通中小学校、中等职业学校教师,《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第十二条第一项、第六项中明确规定了“教师在教育教学管理、实施教育惩戒过程中,不得有击打、刺扎等方式直接造成身体痛苦的体罚行为;不得因个人情绪、好恶实施或者选择性实施教育惩戒”。申请人1作为特殊教育机构工作人员,接受过相关专业技能培训,具备相关专业技能,更应该知道申请人2在学习过程中可能存在沟通障碍及行为无法自控的特点。申请人1明知在对此类儿童的教学过程中可以通过奖励、安抚等更为恰当的方式进行行为纠正,仍因申请人2无法自控,不能正常配合教学,未控制住情绪对申请人2实施击打这一粗暴的行为。且在申请人1在第五次笔录中也陈述了该击打行为没有办法让申请人2配合其上课。结合上述特殊教育场景,申请人1该击打行为明显超出正常教育纠正,甚至教育惩戒范畴,应当认定为殴打他人。
4.申请人1认为其行为不符合“殴打他人”构成要件,被申请人作出的处罚决定违反处罚适当性原则理由不存在。该案中相关证据能够证实申请人1客观上实施了殴打申请人2的行为,申请人1在主观明知殴打他人系违法行为的情况下,未控制住自身情绪,仍对申请人2实施殴打,存在主观故意,申请人2在被申请人1击打后立即号啕大哭,申请人1的行为明显侵犯了申请人2的身体权与健康权。申请人1的行为已构成殴打他人,申请人2系未满十四周岁的残疾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二款第二项之规定,殴打、伤害残疾人、孕妇、不满十四周岁的人或者六十周岁以上的人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并处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申请人1所实施的殴打行为系因申请人2不配合教学引发,对申请人2实施击打一次后便停止,未造成危害后果,违法情节特别轻微,案发后申请人1主动投案并如实陈述自己的违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九条第一项、第四项之规定,减轻处罚,综上,被申请人对申请人1作出行政拘留五日并处罚款壹佰元的行政处罚决定合法有据,过罚相当。
被申请人认为,申请人2认为被申请人对该处罚决定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理由不存在:
1.申请人2提出《行政处罚决定书》一方面认定“现有证据无法证实申请人1殴打申请人2”,另一方面又确认“申请人1对申请人2实施击打一次”,存在自相矛盾的理由不存在。申请人2家属在该案中共提出两部分控告内容:(1)2025年5月16日,申请人1在将乐县某某教育中心对申请人2教学时,存在殴打申请人2行为;(2)申请人2于2024年12月16日曾在将乐县某某教育中心被申请人1殴打。被申请人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中认定“申请人1对申请人2实施击打一次”系对2025年5月16日申请人1殴打申请人2的行为作出的认定。而针对申请人2家属控告的第二部分内容(申请人2于2024年12月16日曾在将乐县某某教育中心被申请人1殴打),经调查,相关证据无法证实,故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中表述为“对于申请人2家属控告的,2024年12月16日申请人1在某某教育中心殴打申请人2的行为,因现有证据无法证实,故无法认定该违法事实存在”,以上系针对不同控告内容作出的不同认定,不存在自相矛盾问题。
2.申请人2提出《行政处罚决定书》仅表述“(申请人1)使用左手手指并拢击打一次”,与客观证据严重不符的理由不存在。经我局民警调取案发监控视频,监控画面显示在2025年5月16日17时11分至17时13分期间,申请人1有使用左手采取手指并拢的方式朝申请人2左侧面部击打一下,并非申请人2提出的三次掌掴申请人2面部。2025年5月18日,申请人2家属到教育机构要求查看监控,后机构两名负责人员(郑某龙、郑某焱)陪同一起查看,经对郑某龙、郑某焱询问,二人均称当日陪同申请人2家属查看监控时,监控画面只显示申请人1只打了申请人2一下。经对残联工作人员余某询问,其称5月18日其也曾查看案发监控,监控显示申请人1打了申请人2一下,后申请人1将申请人2拉到走廊。经询问申请人1,其称当日其有打了申请人2一下,后将申请人2拉至走廊系安抚其情绪,在走廊未殴打申请人2。经查看监控及对上述人员询问,均证实当日申请人1只对申请人2击打一下。经调查,该机构走廊系监控盲区,申请人1将申请人2拉至走廊时,无第三人在场,申请人2提出怀疑申请人1在走廊继续殴打申请人2,无相关证据证实。
3.申请人2提出“现场监控、伤情照片、诊断记录、验伤报告等关键性证据未在处罚决定书中载明,亦未向申请人2及其监护人完整出示,导致事实认定严重缺失”的理由不存在。(1)现场监控已于2025年6月17日对申请人2家属李某某制作第二次询问笔录时向其出示,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中记录为“视频监控录音录像”。(2)伤情照片系民警在办案过程中收集,民警在第一时间拍照制作了原始伤情材料,且于2025年5月20日交由申请人2家属李某某签字确认,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中记录为“申请人2原始伤情记录表”。(3)针对验伤报告,我局民警已于2025年6月9日制作鉴定意见告知书告知申请人2家属谢某某,并同时向其送达鉴定委托不予受理告知书副本,该材料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中记录为“鉴定委托不予受理告知书”。(4)诊断记录由申请人2家属谢某某于2025年6月4日向办案单位提供,我局民警已制作接受证据清单对该材料进行接收,谢某某已签字确认,该材料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中记录为“接受证据清单及材料”。同时对于申请人2家属包某某于2025年6月24日提供的伤情照片等证据材料,我局民警也已制作接受证据清单对该材料进行接收,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中一并记录为“接受证据清单及材料”。上述证据材料均已由申请人2家属确认,且该案处罚决定书中已采信并载明上述证据材料,不存在关键性证据未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中载明及未向申请人2及其监护人完整出示问题。
4.申请人2提出“2024年12月16日,申请人1在同一教室再次对申请人2实施体罚,两次殴打时间间隔不足七个月,属连续侵害,应认定为多次殴打不满十四周岁的残疾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二款第二项加重处罚情形”的理由不存在。因申请人2未满14周岁,且系残疾人,该案中已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二款第二项,认定申请人1殴打未满十四周岁的残疾未成年人。经调查,相关证据无法证实2024年12月16日,申请人1曾对申请人2实施殴打行为,故无法认定申请人1多次殴打申请人2,不存在认定错误问题。
被申请人认为,申请人2认为该案适用法律错误,处罚畸轻的理由不存在:
1.申请人2提出其系未满14周岁的残疾未成年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二款第二项,应对申请人1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并处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被申请人作出行政拘留五日并处罚款一百元的处罚决定明显低于法定下限的理由不存在。该案中已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二款第二项,认定申请人1殴打未满十四周岁的残疾未成年人,因申请人1在案发后主动到城关派出所配合调查,并如实陈述自己的违法事实,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九条第四项所规定“主动投案,向公安机关如实陈述自己的违法行为”情形,且申请人1所实施的殴打行为系因申请人2不配合教学引发,对申请人2实施击打一次后便停止,未造成危害后果,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九条第一项所规定“情节特别轻微”情形。被申请人综合考虑全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二款第二项、十九条第一项、第四项之规定,对申请人1处以行政拘留五日,并处罚款壹佰元,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不存在处罚决定明显行政处罚低于法定下限问题。
2.申请人2提出被申请人忽略其特殊身份及案件社会危害后果,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九条第一项,认定“情节特别轻微”属适用法律错误的理由不存在。该案在处罚认定中已充分考虑到申请人2未满十四周岁,且系残疾人,故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二条第二款第二项,认定申请人1殴打不满十四周岁残疾未成年人,确定量罚档次为“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并处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因申请人1所实施的殴打行为系因申请人2不配合教学引发,并非完全无故对其进行殴打,采取以左手击打面部的方式对申请人2实施击打一次后便停止,实施殴打的方式相对较轻,未造成危害后果(伤情鉴定不予受理),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九条第一项“情节特别轻微”情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九条第一项对申请人1减轻处罚,适用法律无误。
3.申请人2提出其受到心理损害,该心理损害虽无法以体表伤形式固定,但已明显影响其社会功能,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一百一十条所指“精神损害”范畴。该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作出处罚,《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八条规定“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对他人造成损害的,行为人或其监护人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申请人2提出其受到“精神损害”,应要求申请人1依法承担民事责任,该案在向申请人2监护人谢某某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副本时已同时向其告知就相关人身损害赔偿可自行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被申请人认为,申请人2认为该案程序违法,侵害其陈述申辩权的理由不存在:
1.申请人2提出处罚前未书面告知受害人及其监护人有陈述、申辩及申请听证的权利理由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四条规定“公安机关作出治安管理处罚决定前,应当告知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作出治安管理处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依法享有的权利”,第九十八条规定“公安机关作出吊销许可证以及处二千元以上罚款的治安管理处罚决定前,应当告知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有权要求举行听证”。《公安机关办理行政程序规定》第一百六十七条规定“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当告知违法嫌疑人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违法嫌疑人依法享有陈述权和申辩权”,第一百二十三条规定“在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执照、较大数额罚款、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违法嫌疑人可以要求举行听证的其他情形的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违法嫌疑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上述法律、法规中所规定的告知对象均系违法行为人,该案中受害人及其监护人不属于告知对象,不享有陈述、申辩和申请听证的权利。
2.申请人2提出未将鉴定意见、现场监控等关键证据向申请人及其监护人出示并听取意见的理由不存在。该案已于2025年6月9日将鉴定意见告知申请人2监护人谢某某,并向其送达鉴定委托不予受理告知书副本,谢某某已领取相关文书并在鉴定告知书及送达回执上签字确认,不存在鉴定意见未出示问题,申请人2及其监护人在收到鉴定文书后并未提出重新鉴定申请。现场监控在对申请人2监护人李某某制作第二次询问笔录时已向其出示,并听取意见,不存在问题。
3.申请人2提出《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程序存在瑕疵,未向受害人监护人送达副本,导致申请人2无法及时行使救济权的理由不存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七条第二款之规定“案件有被侵害人的,公安机关应当将决定书副本抄送被侵害人”,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七十二条第三款之规定“治安案件有被侵害人的,公安机关应当在作出不予行政处罚或者处罚决定之日起二日内将决定书复印件送达被侵害人。无法送达的,应当注明”。2025年7月17日我局依法对申请人1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民警于2025年7月18日通知申请人2父亲李某某到将乐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领取处罚决定复印件,李某某表示其无法到场,会通知申请人2母亲谢某某到场领取。谢某某于7月18日15时许到达城关派出所,民警在城关派出所一楼调解室内向其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复印件,并告知其就人身损害赔偿部分可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谢某某领取材料后表示对处罚决定不认可,拒绝在送达回执上签字,送达过程使用执法记录仪全程同步录音录像。且申请人在申请行政复议时有向复议机关提交行政处罚决定书复印件,足以证明申请人一方已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副本,不存在申请人提出的送达程序存在瑕疵,侵害申请人救济权利问题。
被申请人认为,申请人2认为该案处理结果显失公正,损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理由不存在。该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作出行政处罚,处罚时已充分考虑被侵害人申请人2未成年人及残疾人身份,故认定申请人1殴打未满十四周岁的残疾未成年人,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二款第二项对其作出处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的立法精神,因申请人1在案发后主动到城关派出所配合调查,并如实陈述自己的违法事实,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九条第四项所规定“主动投案,向公安机关如实陈述自己的违法行为”情形,且因申请人1所实施的殴打行为系因申请人2不配合教学引发,并非完全无故对其进行殴打,采取以左手击打面部的方式对申请人2实施击打一次后便停止,未造成危害后果,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九条第一项“情节特别轻微”情形。被申请人综合考虑全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二款第二项、十九条第一项、第四项之规定,对申请人1处以行政拘留五日,并处罚款壹佰元,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不存在处理结果显失公正,损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问题。
经审理查明:2025年5月16日下午,申请人1在将乐县某某教育中心二楼个性化训练室一内教申请人2写字,因申请人2系持有残疾证的自闭症儿童,在写字过程中无法较好地配合,导致申请人1情绪急躁。17时12分许,申请人2突然大声喊叫,申请人1用左手朝申请人2左侧面部击打一下。2025年5月20日晚申请人2家长带申请人2至将乐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报案,被申请人于同日立行政案件调查。2025年5月21日下午申请人1主动至将乐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投案。2025年6月4日,城关派出所依法委托将乐县公安局物证鉴定室对申请人2伤情进行鉴定,因检材/样本不具备鉴定条件,同日将乐县公安局物证鉴定室作出不予受理决定。2025年7月15日,被申请人对申请人1进行处罚前告知,申请人1提出陈述申辩,2025年7月17日,被申请人针对申请人1的陈述申辩意见进行说明。2025年7月17日被申请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二款第二项,第十九条第一项、第四项之规定,对申请人1处以行政拘留五日,并处罚款壹佰元的行政处罚决定。2025年7月18日,被申请人向申请人2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副本。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廖某某询问笔录;廖某某的陈述与申辩;李某某的报案笔录;余某娟、谢某某、郑某焱、郑某龙、余某、包某某等人的证人证言;李某某原始伤情记录表;提取笔录及照片;辨认现场笔录及照片;接受证据清单及材料;鉴定委托不予受理告知书;视频监控录音录像;到案经过;户籍证明;违法犯罪经历查询情况表等证据证实。
本机关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第一款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被申请人将乐县公安局具有负责本行政区划内的治安管理工作的法定职权,对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行为人有权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本机关认为,被申请人作出的行政处罚程序合法。根据被申请人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其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履行了受案、传唤、调查询问、告知、复核、作出处罚决定、送达等相应的行政程序。申请人2认为被申请人存在程序违法,本机关不予认可。
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四条、第九十八条规定,陈述、申辩及申请听证的告知对象均系违法行为人,申请人2不属于告知对象。因此,申请人2认为被申请人因未告知其陈述、申辩及申请听证的权利属于程序违法无相关法律依据。其次,申请人2认为被申请人未将鉴定意见、现场监控等关键证据向申请人2及其监护人出示并听取意见的情况,本机关认为与事实不符。2025年6月9日,被申请人已将鉴定意见告知申请人2监护人谢某某,并向其送达鉴定委托不予受理告知书副本,谢某某已领取相关文书并在鉴定告知书及送达回执上签字确认,2025年6月17日,被申请人在对申请人2监护人李某某制作第二次询问笔录时已向其出示现场监控,并听取意见。第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七条第二款“案件有被侵害人的,公安机关应当将决定书副本抄送被侵害人”《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送达法律文书的,应当遵守下列规定:(二)除本款第一项规定外,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和其他行政处理决定,应当在宣告后将决定书当场交付被处理人,并由被处理人在附卷的决定书上签名或者捺指印,即为送达;被处理人拒绝的,由办案人员警察在附卷的决定书上注明;……”本案中,2025年7月17日被申请人依法对申请人1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民警于2025年7月18日通知申请人2父亲李某某到将乐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领取处罚决定复印件,李某某表示其无法到场,会通知申请人2母亲谢某某到场领取。谢某某于7月18日15时许到达城关派出所,民警在城关派出所一楼调解室内向其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复印件,并告知其就人身损害赔偿部分可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谢某某领取材料后表示对处罚决定不认可,拒绝在送达回执上签字,办案民警将上述送达情况已记录在案,且送达过程使用执法记录仪全程同步录音录像,但送达回执中办案民警备注时间存在笔误,本机关已要求被申请人补正该证据。因此可以认定被申请人送达程序符合法律规定,并无不当。
本机关认为,本案被申请人事实认定清楚、证据确凿。首先,关于申请人1的行为是否可认定为殴打行为。现场监控视频、申请人1笔录及案件证人笔录等证据可以体现,2025年5月16日17时许,申请人1用左手朝申请人2左侧面部击打一下,存在明显发力,监控视频中可以听到击打发出“啪”的一声较大声响,击打过后申请人2便开始号啕大哭,可以判断出该次击打存在明显发力,因此客观上可明确申请人1实施了殴打申请人2的行为。主观上结合现场视频中申请人1的言行及其在多次询问笔录中均陈述其因急躁未控制住情绪故打了申请人2,其在询问笔录中亦陈述该行为已经超出了对待此类自闭症学生的教学举措,对教学没有帮助,而申请人1作为特殊教育机构工作人员,接受过相关专业技能培训,具备相关专业技能,应该知道申请人2在学习过程中可能存在沟通障碍及行为无法自控的特点,仍因申请人2无法自控,不能正常配合教学,未控制住情绪对申请人2实施击打这一粗暴的行为,因此,可以认定申请人1在主观明知其行为已超出正常教学举措情况下,未控制住自身情绪,仍对申请人2实施殴打,存在主观故意,申请人2在被申请人1击打后立即号啕大哭,申请人1的行为明显侵犯了申请人2的身体权与健康权。综合上述情形,被申请人认定申请人1的行为已构成殴打他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其次,申请人1提出的“现场证人仅有余某娟”,行政处罚决定书中的谢某某、郑某焱、郑某龙、余某、包某某等人不属于本案证人的理由本机关不予采纳。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三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凡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余某娟、谢某某、郑某焱、郑某龙、余某、包某某均对该案情况有所了解,因此被申请人认定余某娟等人均系本案证人符合法律规定。申请人1提出的“证人中“张某某”是谢某某”问题系笔误,属轻微瑕疵,不影响案件事实认定。且民警在发现该问题后,已立即纠正并重新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申请人。第三,关于本案申请人2受伤害结果的认定问题。本案中,对申请人2伤情,因检材/样本不具备鉴定条件,将乐县公安局物证鉴定室作出不予受理决定,2025年6月9日被申请人告知申请人2不予受理结论后,申请人2未提出异议。而该案“伤情记录表”中虽记录申请人2左边鬓角处有一道2至3公分的划痕,在后续调查过程中,申请人1亦陈述称该划痕确系其造成,但无法确定系在殴打过程中造成还是其在为申请人2擦鼻涕过程中造成,现场监控视频及询问笔录等证据均无法证实划痕形成的具体原因,综合上述情况,被申请人认定“未造成危害后果”,本机关予以认可。第四,关于申请人1是否构成多次殴打申请人2。申请人2主张,2024年12月16日,申请人1曾对其实施殴打行为,其已构成多次殴打他人。证明2024年12月16日案件事实的现有证据有申请人2姐姐包某某提供的2024年12月17日申请人2的受伤图片及其与申请人1的微信聊天记录,微信聊天记录内容无法直接体现申请人1有殴打行为,亦无法体现申请人2的受伤是申请人1的殴打行为造成,经被申请人调查,该时间段现场视频监控已被覆盖,无法提取,且申请人1当时与申请人2系一对一教学,无其他人员在场,综合相关证据无法证实2024年12月16日申请人1曾对申请人2实施殴打行为,故被申请人认为无法认定申请人1多次殴打申请人2,本机关予以认可。第
本机关认为,本案被申请人法律适用正确,过罚相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二款第二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并处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二)殴打、伤害残疾人、孕妇、不满十四周岁的人或者六十周岁以上的人的;”第十九条第一项、第四项“违反治安管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减轻处罚或者不予处罚:(一)情节特别轻微的;(四)主动投案,向公安机关如实陈述自己的违法行为的;”本案中相关证据能够证实申请人1的行为已构成殴打他人,且申请人2系未满十四周岁的残疾人,但鉴于申请人1所实施的殴打行为系因申请人2不配合教学引发,且综合现有证据申请人1实施击打一次后便停止,未造成危害后果,违法情节特别轻微,案发后申请人1主动投案并如实陈述自己的违法行为,因此,可以认定被申请人依据上述事实对申请人1作出行政拘留五日并处罚款壹佰元的行政处罚决定合法有据,过罚相当。
综上,本机关认为被申请人在行政处罚过程中,依法履行了立案、调查、询问、辨认、送达等行政处罚程序,根据该案调查取得证据材料,结合治安违法情节对申请人作出了行政处罚决定,该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八条,本机关决定如下:
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将公(城关)行罚决字〔2025〕0014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如不服本决定,可在接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5年9月12日
扫一扫在手机上查看当前页面






